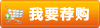|
关于我们
 新书资讯 新书资讯 新书推荐 新书推荐 |
西南角——民国文人抗战年月的那些事
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之国脉,十几所院校和研究机构战时先后迁入云南,昆明一时间人文荟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全国相当数量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知名人士,都在云南这块偏僻的红土地上会集了。他们不失民族气节,甘于艰苦,甘于淡泊,朝夕系念着教学和科研,严谨治学,诲人不倦,为培养人才而作着不懈的努力。在他们心目中,无论环境如何艰苦,无论敌人如何摧残,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让民族的“学术生命”倔强地存活下去。本书挖掘出大量新史料,超越以往关注西南联大的视角,观照更广阔的时空,更多的学者文化人的群体,以丰富的细节再现彼时大西南弦歌不辍、延续民族文脉的精神坚守之状貌,给今人留下了无尽的怀想。
细看“云归派”抗战年月的那些事,感受苦难中大师们的坚守与担当
张维,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执教二十余年,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地方文化史研究之余,多年来致力于名人传记的写作,已出版传记作品二百多万字,主要著作有《熊庆来传》《李广田传》《楚图南传》《袁嘉谷传》《云南名人的青少年时代》等。曾多次获全国及省级奖励。
《西南角——民国文人抗战年月的那些事》目 录引言第一章 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昆明的外省人一、古典文学专家施蛰存二、青年“明史学家”吴晗三、“战国策”派的一位主将——林同济四、“不被云南人欢迎的”文学评论家李长之 第二章 高等学府的两位领航人一、西南联大常委主席梅贻琦二、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第三章 蒙自南湖边来了一群文人一、初到蒙自的联大师生二、爱上这座小城的朱自清三、“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 四、在南湖边沉吟的陈寅恪五、“天南精舍”七教授 第四章 两位才女的“昆明缘”一、林徽因两度到昆明二、在昆明住过两个春秋的冰心 第五章 大师们的“雪泥鸿爪”一、赵元任来去匆匆二、曹禺亲自执导话剧三、巴金的昆明之恋四、为友情而来的老舍五、徐悲鸿开画展劳军第六章 联大师生中的作家、诗人一、穷得有骨气的朱自清二、寄寓云南九年的沈从文 三、把昆明视为“第二故乡”的冯至四、“不只暴露黑暗,更要歌颂光明”的李广田五、悲壮的“九叶诗人”穆旦 六、昆明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汪曾祺 第七章 苦难中的学界大师一、“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的陈寅恪二、幸遇“从不易得的群英会”的吴大猷三、岩泉寺中静心写作《国史大纲》的钱穆四、六年“闭门精思”的陈省身五、隔帘而居伏首搞数学的华罗庚第八章 早期的“民盟”贤达们一、奋力推动民主运动的楚图南二、用生命写下绝笔的闻一多三、从学者变为民主斗士的吴晗四、在昆明度过“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的费孝通五、学术生涯从这里起步的吴征镒六、激情诗人光未然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战国策”派的一位主将——林同济
林同济是这第一批到昆明的外省人中留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他是被熊庆来校长从天津的南开大学聘到云南大学担任文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经济系主任的。 个头不高的林同济1906年出生于福建福州的一个望族世家,此时也不过三十一岁,可是就已经有一番令人刮目相看的学术经历了。到了昆明之后,他又一再发表坚定抗战的言论,并与雷海宗、陈铨一起合办了《战国策》半月刊,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一场文化学术思想浪潮,表达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张。他们被人称为“战国策”派。 林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身为前清进士的祖父给予了他很好的童年启蒙教育。在举人出身的做过民国司法官员的父亲影响下,聪颖的林同济打下了深厚古文功底。刚满十四周岁时,开明的父亲就把他送入新学堂学习,让他在接受更多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接受西学启蒙。1922年,林同济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饱受中西文化的浸染。1926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公费赴美留学,进入安阿伯密西根大学学习,主修国际关系与西方文学史,侧重研究社会政治思想。两年后他顺利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院政治系学习两年,取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接着他继续攻读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边读博士边担任该校东方学系讲师,并兼任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米尔斯学院“中国历史与文明”讲师。这期间,西方思想界掀起的“尼采热”的浪潮,给林同济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34年,年仅二十八岁的林同济获得了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日本在东北的扩张》答辩十分成功。1935年,林同济归国任教于天津的南开大学,被聘为政治系教授兼经济研究所导师,同时并被聘担任英文刊物《南开社会经济季刊》主编。 青年林同济立志“做个思想家”,一是因为从小就被祖父灌输了中国传统推崇的“三不朽”中“立言”是最高的、最可久远相传的思想,二是受西方推崇的“思想家是最有为的政治家,因为它控制着人们的灵魂”的观点的深刻影响。他学成归国后,便效仿费希特《告德意志人民书》的风格,着手构思写作一部批判中国文人性格的著作。可惜,抗战的爆发使他的写作中断了。 就在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为了取得更多的支持,在庐山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亲自主持座谈讨论。全国有影响的一些知识分子应邀出席,林同济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著名学者胡适、陈岱孙等均在受邀之列。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想将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争取他们的支持,让他们为抗日战争作好准备。会上,蒋介石宣布对日全面抗战。蒋介石表示,中国只有抗战,更只有抗战到底。会议结束时每个与会者都被“邀请”加入国民党。当时要拒绝那个“邀请”是很难的,因为是蒋介石在亲自主持座谈会。但是林同济拒绝了,他历来的信念就是“君子不党”。 林同济到云南大学任教时,是独身一人来的。他新婚才一年的美国籍妻子黛南?格雷还留在南开大学。黛南是林同济留美期间兼任米尔斯学院“中国历史与文明”讲师时的学生,她仰慕这位儒雅的才识出众的来自中国的讲师,两人相恋了。黛南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受父亲影响,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是增进黛南与林同济的感情的一个因素。林同济与她1936年在东京相聚成婚,但特意把婚礼庆典安排在中国举行。随后,黛南也到南开大学教授英文。抗战爆发后她辗转逃到上海,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躲过了日本人的迫害。 林同济一生对从政当官毫无兴趣,但对国家、对政治却非常关心。他同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学成归国,想以学到的知识报效国家。林同济为自己设计的角色是一名独立于政治权威的公众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站出来为大众说话,如有必要时还要向当权者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成了他一生的信条。 1937年秋,林同济到云南大学就任文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经济系主任后,除主理学院及系里的事务、给学生讲课之外,还很快就开始在云南舆论界发出了他的声音。11月28日,他在《云南日报》发表《抗战成绩的一个估量》的文章,就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而于11月20日移驻重庆一事,表明自己的看法:“国府移驻重庆,不是仓惶之举,乃是筹定之计;不是退缩,乃是决心;不是抗战的临终,乃是抗战的正式开幕。大陆国的农业民族所以抵抗工业化的岛国侵略者,奉有其特殊的战略在。此后抗战形势的展开,必将要益显出此种特殊战略的性质。”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说:“我们唯一的任务,唯一的国策是战!战!战到底!” 几个月后,1938年3月间,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由重庆来到昆明,在教育界人士的欢迎会上讲了一席话,林同济听后感触尤深,他在13日《云南日报》发表的《论中等以下教育之重要》一文中写道:“张伯苓先生……说了几句话,意义特深:‘敌人杀得愈横暴,我们干得越起劲。抗战局面愈紧张,我们教育的推进愈要积极。高等以上的教育必须推进,中等以下的教育尤当推进!’这位身高六英尺六十三翁,四十年前是个创办中国教育的先锋,直到今天,仍是教育界的巍然领袖。上面的几句话,活现出此老勇往迈进的精神,并指点出中国此后教育开展的方向。” 接下来,1938年4月16日,云南各界民众代表二千余人举行讨逆宣传大会。林同济在会上发表了演讲,详细论述了对于汉奸之认识、汉奸产生的原因、铲除汉奸的方法。 一个星期后,云南省各界热烈举行反侵略宣传大会,出席的有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约二千人。云大校长熊庆来做大会主席,林同济和另外几位知名人士作了演讲,表达了同仇敌忾的激情。 这些文章,这些演讲,都让人感受到林同济那满腔的爱国激情和鲜明的民族主义情怀。1938年9月18日,林同济在全省各界举行的“九一八”国耻七周年纪念会上又热情地发表演讲说:“‘九一八’是我国历史上的大悲剧,同时也是一幕大壮剧。因为它给我们的刺激太大!试想东北三省土地之大,为德、法两国土地之和,而数日之间,就完全沦陷,真是创巨痛深。从此,全国才有深刻的觉醒,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在‘九一八’后,大家的眼光才转变,一致对外。所以‘九一八’给我们的教训,可以说是树立了新的政治观,就是目光对外的政治观,才认识国防的重要。” 林同济的这些文章和演讲在昆明大后方不断地在产生影响。不过,林同济更大的影响,是他作为“战国策”派主将之一,出现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视野中。 1938年夏天,西南联大文法学院由蒙自迁回昆明后,让林同济遇到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友人。这一年,联大教授雷海宗主办的《今日评论》在昆明创刊。他邀请林同济、朱光潜等人参与编辑。时间不长,《今日评论》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成为后来“战国策”派的基本力量。 在西南联大带来的那种学术氛围影响下,林同济开始考虑办个刊物,想通过刊物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用充分的表达和鲜明的观点,掀起一场文化学术思想运动。1940年4月,林同济与陈铨、雷海宗主编的《战国策》半月刊创刊,迅速得到联大、云大诸多学者的支持。贺麟、朱光潜、冯友兰、陶云逵、沈从文、费孝通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聘为刊物的特约撰稿人。“战国策派”因之而得名,这二十六位“特约执笔人”被称为“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林同济被公认为“战国策”派的核心人物,他提出的“战国时代”、“尚力政治”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战国策》也是因同那篇著名的、很有争议的文章——《战国时代的重演》而得名。 刊物创刊后,主持人是林同济和何永佶,何是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缪云台的秘书,他说动了缪云台出钱支持刊物印行。后来,因空袭频繁、印刷困难、物价飞涨等问题,刊物于1941年4月宣布停刊。而后,林同济得到设在重庆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支持,从1941年12月开辟了《战国》副刊,每周一期,编辑部设在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直至1942年7月,共出版了三十一期。 “战国策派”的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们,有着迫切的“救世之心”,他们的初衷是“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旨”,致力战时的文化重建。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世界民族生存竞争中保存自己的民族。他们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要重新铸造“民族精神”,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他们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强调民族精神的“力”——这一点后来被一些人认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加以指责,甚至进行强烈攻击。这也成了林同济等人后来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罪证”。 林同济对学术的追求、对政治现实的关注始终是执著的。从1941年5月下旬开始,在林同济的主持下,云大政治经济系为增进学生对现代学术思潮及问题的认识起见,特举办三大系统的学术演讲,包括:1. 现代思潮十讲,2. 中国问题十讲,3. 各国情势十讲。先举行现代思潮十讲,聘定十位主讲人为雷海宗、冯友兰、肖蘧、潘光旦、吴宓、陈序经、陈铨、贺麟、王赣愚、林同济。另外两大系统聘定主讲人钱端升、陈岱孙、陈达、陈雪屏、何永佶、王信忠、伍启元等,并决定在每系统演讲完后,即将各讲演词由政经系汇编成册。这一阶段,林同济的代表作主要有《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虔恪》等。 1942年,林同济的婚姻生活不幸以“悲剧收场”。随着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美国籍妻子黛南?格雷躲在上海的那座避难所也无法保留了。此时,急于赶到昆明和林同济团聚的黛南,只身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有时走路,有时骑马,历尽艰险,在路上竟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见到林同济时她已感身心交瘁,接下来她又完全不能适应昆明的环境。这里没有自来水,蚊子很多。黛南得了慢性腹泻和急性疟疾,健康出了问题。几个月后,她的身体可以说是被拖垮了,而昆明的医疗条件又极为糟糕。于是,林同济不得不痛苦地建议她回美国,觉得“这是唯一救她的法子”。同时,考虑到黛南还很年轻,而两人再相会的机会也许非常渺茫了,林同济提议离婚。黛南在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后,最终也同意离婚。她离开了昆明转道越南回到了美国。此后一段时间里,林同济得了严重十二指肠溃疡。他的弟弟林同奇认为——“婚姻生活的悲剧收场肯定是个重要的诱因”。 这时,复旦大学已搬迁到北碚这个重庆旁边的小镇,林同济的父亲已在复旦教授民法,一家人都到了北碚,于是,身体状况不太良好、内心痛苦的林同济也离开了云南大学,转入复旦大学担任比较政治学教授,得以在北碚常与家人团聚。 (摘自张维著《西南角——民国文人抗战年月的那些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定价:35.00元) 书摘2: “不被云南人欢迎的”文学评论家李长之 来到昆明的第一批外省人中,还有一位清华大学留校任教刚两年的青年才子李长之。他接受云南大学之聘后,在炮火硝烟中离开北平,经济南到南京又转往汉口,乘火车南下广州,然后取道香港,搭渡轮赴越南,辗转近两个月才到达昆明。 可是,在他到昆明仅半年多后,便闹出了一桩当时在大后方轰动一时的“李长之事件”。这个一袭蓝布长衫、头发蓬松、不修边幅、样子潇洒的年轻人,成为了“云南人不欢迎的人”——用施蛰存开玩笑的话来说——“被云南人驱逐出境”了。 为什么会被“驱逐”,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仅仅是因为他写了一篇短文——《昆明杂记》(共十一则),发表在1939年5月广州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第六十七期上。 李长之是山东利津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秀才,念过山东高等学堂,文言功底深厚,写得一手好古文,又懂英文和法文。李长之家教渊源深厚,本人天资聪慧,十二岁时开始写新诗,这一年写的诗歌《早晨的大雨》和散文《森林的话》、《我的学校生活谈》便分别被《儿童世界》和《少年》杂志刊发。 1931年,二十一岁的李长之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入哲学系。学习本专业的同时,他还受到校内德国文学教授杨丙辰的影响,喜爱德国古典美学,并从中受到浸润,获得了宽阔的眼光和开放的胸襟,培养了充满激情的独立精神。他意气飞扬,才华横溢,不断有新文章发表。最厉害的时候,曾一天写出了一万五千字的长文。 1934年秋天,他和杨丙辰创办了双月刊《文学评论》。这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夜宴》。次年,他应邀开始主编《益世报》的文学副刊,并在该副刊上连载发表了自己写的《鲁迅批判》。同年李长之毕业留校任教,与钱钟书、张荫麟、陈铨一道被誉称为“清华四才子”。 李长之在十七岁至二十六岁期间从事文学评论的初始阶段中,著文批评了卞之琳、老舍、张资平、茅盾、梁实秋、臧克家等人的作品。 1936年1月,在赵景深的大力支持下,《鲁迅批判》的文稿由北新书局初版。在该书中,李长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求真的目的,以一种独立的批评精神对鲁迅进行了评论,充分肯定和热情赞颂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但也绝不虚美饰非。这部不足十万字的书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系统的专著,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青年李长之一举成名,也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批评家的地位。该书迄今为止仍是鲁迅研究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之一。 李长之身材瘦小,不像一般山东人那样个头高大,但性格却是地道山东人般的真诚爽朗,耿直豪放。 1937年,李长之因对德国古典美学情有独钟,准备去仰慕已久的德国留学。他都已经走到边境了,可是却接到当地政府通知,说出国前必须承认“满洲国”,并且还要改道东北才能离境。坚持自己人格操守的李长之,不愿接受必须承认伪满政府才能留学的这个“污秽、丑陋”条件,果断放弃留学。 如果他不放弃留学,那他也就没有机会被熊庆来聘到昆明来了。 9月下旬,李长之到云南大学报到后,也住进了学校安排的临时教师宿舍。起初,他对昆明印象还不错,说这里大体上与内地的几个省城没多大的分别,并不是某些中国人印象里的“不毛之地”,也不像某些外国人所描述的那样神秘,说它是象牙古玩珍奇东西的出产地。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赞美昆明的房屋“很洁净而精致”、“幽静而疏朗”,石板铺就的街道“很坚固,平稳而美观”,夸奖“云南人很淳朴,忠厚”,“云南的青年是极好的,体格很健壮,精神很勤奋。肯做,肯切实,一点也不浮嚣”。 可是,时间不长,他便对昆明的环境和气候、对昆明慢节奏的工作和生活感到有些不适应了。出于天真率直的个性,他把自己对昆明的失望,无所顾忌地写了一篇《昆明杂记》,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对昆明的天气,他在文章如此抱怨道:没到这里的时候,便想象这里的天气之佳。别的不说,总是希望在工作上更有效率。然而不然,天气诚然不错,但是偏于太温和了,总觉得昏昏的,懒洋洋的,清爽的时候不过早晨和夜里。就工作上来说,我觉得远不如北平。我甚至十分怀疑,是不是在这里住下去,将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他在《昆明杂记》里说,在昆明最喜欢的是牛,这因为“中国人所具的种种美德,发现在牛的身上。沉着,忠厚,宽大,耐劳,虽然是中庸的罢了,然而有潜藏的深远的力量在”。他进而论及昆明的人,说“这里的人很笃厚”、“可爱”、“很虚心,但又有一种潜藏的深厚的进取的心在准备着”。作者还用其他城市和昆明相比,说汉口“浮夸”,香港“一点人味也没有”;而昆明呢——李长之批评说——昆明人“懒洋洋的”,工作缺乏“效率”。 对于这个“论点”,李长之举出了充分的“证据”:一是他请一位木匠做一个书架,他急等着使用,“本来说好是五天送来的,但是隔了一个月还没送来”。这严重“阻碍”了他的工作步伐。二是他到云南省图书馆借阅图书,发现书目编写得很混乱,查阅起来极不方便,而且“上午十一点才开馆,下午四时半就闭了”,晚上也不开馆。更严重的是,借书时好不容易把想要的书目查出来了,但自己不能填借书单,要交给馆员去填,可是馆员在填写时“又要像阿Q那样惟恐画圈画得不圆的光景,一笔一画,就又是好些时候,书拿到,便是快要闭馆了”。他对此难以忍受。三是他看到马市口世界书局的门旁那个宣传橱窗里贴着一些用自来水笔所作的“广告和抗战的漫画”,可是从他到昆明已经半年了,未见橱窗里的内容更换,可是每晚8点钟依然有“成堆”的“热心观众”津津有味地往那窗里“争着瞧”。这真是让他想不通的怪事。 可以说,李长之对昆明非常失望。他是在失望之中写出了《昆明杂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38年5月的《宇宙风》上,而4月正是滇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英勇作战,军威大振的时候。昆明人正为滇军的英勇而扬眉吐气感到余兴未尽,也正在为打通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而竭力苦干之时,李长之却写出如此“不友好”的文章,不少昆明人对此确实不满了,甚至生气了。 据说,云南省主席龙云对此也很生气,还不怎么高兴地对熊庆来讲了几句让他“今后聘用人时要注意”之类的话。“云绥公署”也表示欲请李长之“去谈话”。当时,昆明的《民国日报》和《云南日报》等大小报纸,也“群起而攻之”,发表了多篇回击李长之的文章。这让李长之感到“大恐”,觉得在云南已无法立足,不得不离开昆明,悄悄地“逃之夭夭”了。 1938年6月,颇有几分“被云南人驱逐出境”意味的李长之,乘汽车经贵阳到重庆,进入了中央大学任教,同时受聘于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后来,李长之以著名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的身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平心而论,《昆明杂记》中说到的昆明人极其“散漫”和“古板”的工作状态,也并非不是事实。可是这“事实”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没有得出李长之那样的感受。比如在李长之走后不久来到昆明读西南联大的青年学生汪曾祺,同样进到李长之笔下提到的这个图书馆,甚至同样遇到了那一个图书管理员,然而,在汪曾祺笔下,却是这样一番有趣的味道: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很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有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当年写的一些昆明题材的散文,如《怀昆明》和《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过节和观灯》之二)等,与李长之写的那篇《昆明杂记》也都很不一样,不像李长之那样对昆明怀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或偏见。看来,怀着不同的心境,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事物时,是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的。 诚然,当年一些昆明人对李长之那篇《昆明杂记》——用如今的说法——是有些“反应过度”了。即便是在云南籍的文化人楚图南看来,也觉得不该那样对李长之大加挞伐。楚图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写的《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一文里,反思这“李长之事件”说——不要只听“学者名流”夸云南天气、社会好得像天堂一样的恭维话。对于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使学术思想能自由健全地发达起来,云南才能迎接伟大时代的到来。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