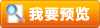|
关于我们
 新书资讯 新书资讯 新书推荐 新书推荐 |
非洲农业的转型发展与南南合作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非洲农业的最新发展与内生动力”,从大陆内的政策和激励机制、外来援助、投资与商贸合作分析以及不同层面的创新实践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为“新兴市场国家对非农业南南合作”,主要讲述了巴西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马拉维进行农业合作的不同情况;第三部分为“中国对非洲农业合作的新型实践”,中国对非农业合作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完全不求经济回报的单纯援助,援建大型农场,到目前的援助、贸易和对外投资并举的阶段。
"序言 非洲农业的转型发展与南南合作
刘海方
虽然非洲农业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尤其是其自然条件,但受历史遗产、基础设施和资本积累的限制,其发展仍相对不足。这不仅对本地乃至世界粮食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也影响了非洲整体经济结构的升级。
非洲农业大体可以分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两种类型,传统农业指自给自足的维生农业,从参与的人口比例来讲仍然是非洲目前的主要生产方式;现代农业则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纳入政府可控制的国民经济体系、真正的第一产业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同时也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重要支持的商业化的农业。21世纪以来,非洲的快速发展被认为主要是由世界大宗原料商品价格优势推动的,非洲国家再次意识到当前急需进一步进行整个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升级,以便完成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其中,以农业的转型升级尤为重要。对此,非洲的政治经济界精英已经达成共识,正如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的领导人卡洛斯博士在其最近的文章中所言,“历史证明,成功使人民脱贫的国家都依靠了农业革命,对粮食的生产、仓储、加工、销售和使用都进行了系统的改进。从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欧洲国家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贡献巨大。农业革命影响国家经济的著名例子是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它们利用农业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非洲急需学习中国、巴西和印度是如何在农业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的,而且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实现大规模人口的减贫。”
一 非洲农业发展轨迹:从“结构调整”方案到自主探索
农业是非洲大陆经济转型的关键领域之一,却长期被忽略和误导。获得独立之初,非洲国家急欲摆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于是按照依附论的主张纷纷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国家财政主要支持工业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常常忽略甚至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初,非洲国家在财政压力之下相继转向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e Adjustment Programme),尽管对于以往忽视农业的政策有所调整,但更重要的,还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重心放在了对于“自由市场”的打造上,即按照经济学教科书塑造一个标准的宏观经济环境。然而这种强调产权保护、保障合同顺利实施的宏观环境,更多的只是有利于外来公司的发展;而对外开放市场使非洲国家刚刚开始萌芽的民族产业受到极大的冲击(1980~200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6%下跌到12%),与此同时,非洲农产品贸易环境急剧恶化,开始更大程度地受到外部市场价格震荡的影响,完全无法与欧美国家政府补贴的经济作物抗衡。20世纪90年代非洲农产品出口数量增加,收入却在下降,有学者统计,如果1980年的单位出口价值为100的话,非洲在1990年和2000年的单位出口价值分别下跌到81和84。
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出口还是增加了30%,例如,肯尼亚的茶叶出口已经占到肯尼亚出口创汇的20%,花卉种植业也每年增长15%~20%。南非这样的矿业出口创汇大国,农业也一直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上,如果再加上中下游的农业加工业,农业总的构成应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总之,农业成为非洲各国的主要收入来源。马拉维商会联合会(Malawi Confederation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MCCCI)2010年的报告称,农业是马拉维经济的主要支柱,构成该国经济增长的33.6%。
近年来,非洲的农业发展更是亮点纷呈。例如,加纳政府引进农业机械,让小农户实现了成片耕作,政府的介入成功地将这个国家变成了“面包篮子”。在乌干达,鱼产量大幅上升,2005~2015年增长了35%,水产品从1999年的285吨猛增到2012年的10万吨以上。埃及2013年的稻谷单产量达到了每公顷9吨,名列世界第一,2014年总产量达到750万吨,带来约5亿美元的收入。坦桑尼亚在低地地区成功推广了蓄水灌溉系统,从而改善了依靠雨水灌溉的水稻种植。在低成本个体抽水项目的帮助下,尼日利亚农民采用小型灌溉设备,旱季用吊杆或葫芦从河边抽取浅层地下水浇灌蔬菜,供应城市居民。肯尼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奶制品业最发达的国家,每年产量可以达到20亿升。如果综合非洲农业的起点和独立以来的坎坷发展历程以及目前政府体制方面的局限性,非洲的农业已经取得的成绩是必须被承认的,而且也说明其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引入支持非洲的农村发展项目,大规模引进现代农业技术,用于种植业和动物饲养,其中包括高产作物、化肥、农业化工、贷款、机械化和灌溉业。令人遗憾的是,因为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这些项目不但缺少综合收益,而且很多不能持续下去。这个教训被非洲领导人所汲取。2003年非洲联盟(简称非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批准了“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omprehensive Africa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rogramme,CAADP),表明了非洲领导人对于农业主导的发展方向的决心。该项目规定,每一个非洲国家的年度预算至少要有10%用于发展农业,才能真正完成解决粮食安全和减贫的目标。然而,目标从非盟层面向各个国家落实并不容易,除了少数几国,非洲国家的农业投入一直低于该目标。尽管如此,“非洲综合农业发展项目”作为第一个非洲人自己设计出来的、集体治理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非洲各国目前制定各自农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和蓝本,而且迄今该项目所发挥的凝聚共识、动员力量、提升能力的作用还是非常显著的。
二 综合治理方案的出台:农业商业—农业加工—工业化的路径
在近代历史上,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主要靠石油、天然气和矿产支撑。然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在非开采行业的扩大上,特别是那些能够推动创新、满足国内供应链以及促进出口的产业。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几经摸索实践,经济发展的思路也从原来只专注于进口替代品工业到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自由市场”建设,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自主探索进行经济治理的新工业化思路,特别是自2013年非盟2063年议程发表以来,经济转型的概念被不断强调。领导人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专注于建设“自由市场”,国家对本国产业的扶植和保护一直都是需要的。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并没有使非洲经济发展与欧美世界“共衰退”,而是随着整个亚洲的向好趋势在“共繁荣”,“非洲崛起”也自此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非洲狮子似乎已经真的不可逆转地奔跑在“后发优势”的迅速发展之路上了;但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一路走跌,大多数依赖单一资源产品(包括金属和非金属矿业品和农产品)的非洲经济体都遇到明显的困难,这使非洲领导人又一次不得不清醒并痛彻地面对这样的事实:非洲经济的结构必须调整,否则永远被自己不能左右的世界市场价格机制玩弄于股掌之间。
怎么调整呢?20世纪60年代单纯提倡工业化的思路已经有教训摆在那里。显然结构调整需要一个综合治理的思路,非洲国家要明确自身优势,然后找到适合的切入点,迅速跻身并提升自己在世界价值链上的位置。对于大多数还是专业生产主导的非洲国家来讲,从农业产品入手,振兴有优势产品的加工业,利用产业的上下游链条延伸至其他产业,带动运输业、服务业、商业甚至更高端的制造业的发展,正是优势所在。
1989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首脑会议上,非洲国家开始认真反思并接受结构调整方案的发展战略,这次会议决定,每年的11月20日作为“非洲工业化日”,联合国大会也给予承认并将其提升到联合国层面。此后,每年的“非洲工业化日”的具体主题有所不同,但都是在非盟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之下为非洲国家提出的集体发展目标。2013年,“非洲工业化日”的主题是将工业化与经济转型结合在一起,同时会议报告的封面很有启发意义,表达了非洲国家处在世界大宗商品价格顺风期、希望借机实现完成经济转型的目标,以便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有趣的是,通常所说的资源的概念,不再狭隘地定义为矿产资源,而是被有意地宽泛化为“自然资源”——特别是事关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和水源被列为更重要的考量范围。2014年“非洲工业化日”的主题不再是以往发挥矿业资源优势。会议提出了发挥非洲农业优势并向工业化方向努力,同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目标。
上文论述了整体发展战略的逐渐试错并逐步达到全面、各部门协调考虑的过程,它体现了非洲在经济治理方面的认知过程;农业方面的具体政策框架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外来政策干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非洲领导人也曾经自觉不自觉地长期忽略、牺牲农业发展,无论是公共开支还是政府发展援助,大量资金被错误地分配,没有满足农业的根本需要。例如,2002年非洲获得了7.136亿美元的政府农业发展援助资金,几乎是东亚和南亚国家的两倍,后两者只得到了4.798亿美元。然而,非洲获得的援助资金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回报。
如上所述,非盟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14年联合发表的报告提出非洲农业转型关键的第一步:应从商业而非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入手来提高生产率。报告认为,非洲绝大多数小农户生产效率低,也不赢利。他们一直只能勉强糊口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生产的农产品产量低、品质差,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因为大部分人缺乏了解现代技术和促进生产的信息渠道;二是农民与产品市场脱节——糟糕的基础设施使农产品上游的生产与下游的加工销售几乎不能联系起来。总之,从维生农业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型,是个系统治理的工程,核心是利用可获得的资源来获取应用技术、提高生产力。这包括培育新的种植作物和动物的种类,实现农业机械化、实施土壤和水源综合治理战略,综合治理病虫害,进行农产品加工以提高附加值,以及促进社会和文化行为的变化适应。另外,在发展过程中,有倾斜性地解决大多数农村人口的贫困生活条件,改善农民和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
在自下而上的层面,非洲的有识之士也在积极推动农业的研究和发展。卡罗·B.汤普森教授的研究涉及南部非洲小农户的贡献,戴安娜·李-史密斯研究员关于《城市农业》的讨论也显示出了非洲国家的社会组织和公众对于这些“本土方案/非洲方案”的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非洲一些农业科学家在从事援助工作的国际人士的支持下,发起了“非洲农业研究论坛”(Forum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Africa,FARA),这个民间组织1997年正式成为世界银行研究非洲农业发展在非洲大陆范围内的合作伙伴。在制定“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过程中,民间组织也贡献良多。如今,这一论坛已经成为非盟的专门技术机构,其最新的成果就是非洲人自己制定和领导的“农业科学议程”(Science Agenda)的设立。这个论坛能够凝聚非洲知识精英、保持和提升非洲人在农业发展和科学研究方面的能力,从而使非洲的农业发展真正受惠。
2014年被非盟命名为非洲的农业和粮食安全年,显示了非洲国家振兴农业的决心。非洲农业研究论坛作为协调机构,依照辅助性原则,将非盟的计划分解为次地区的和各国的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论坛动员非洲大陆范围内的各个相关项目机构,与国际范围内的利益相关方一起,共同针对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机会和挑战采取行动。目前,非洲农业研究论坛在各个国家的合作伙伴包括非洲新农业技术推广(Dissemina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in Africa,DONATA)、非-欧农业研发伙伴平台(Platform for African-European Partnership on Agricultural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PAEPARD)、地区农业信息学习系统(Regional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Systems,RAILS)、撒哈拉以南非洲挑战项目(Sub-Saharan Africa Challenge Programme,SSACP)、农业创新商学研组织(Universities,Business and Research i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UniBRAIN),等等。对于刚刚设立的“农业科学议程”,论坛也采取类似的流程运作,与已经成立并运作的非洲大陆范围内的农业相关研发机构合作,共同推进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具体已经选定的合作伙伴包括农业适应未来要求组织(Adaptation for Future Demands in Agriculture,AFDA),非洲环境和农业研究特别项目(African Special Progamm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Agricultural Research,African SPEAR),非洲农业集约化纲要(Programme for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Africa,PAINT),非洲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和农业企业家共筑粮食安全框架(Africa Human Capital,Science Technology and Agripreneurship for Food Security Framework,AHC-STAFF)等。
笔者在加纳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非洲国家的农业科学家在推动农业革新、连接农民的生产和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加纳的17个小型农业研究机构构成了一个大的理事会。加纳甘蔗农多年来苦于田鼠的破坏。在研究机构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将这种偷食甘蔗的田鼠培育、改良成为人们可食用的饲养动物,从而将农业天敌转化为与农作物共生的食用动物蛋白来源——这不能不说是非洲人自己的农业创新技术。该理事会遍布加纳全国的网络将这一技术迅速推广出去,以至于加纳街头很快就可以看到买卖交易这种田鼠的农民了。
三 发展模式之争——小农户还是大公司?
独立以后,大部分非洲国家农业发展迟缓甚至出现倒退,究其原因有一些是殖民时期以来形成的深层观念的影响。为了宣扬殖民占领的合理性,20世纪上半叶就出现了为白人占地辩护而炮制的“空地说”(其实是非洲人的公社土地在休耕,但被解释为空地);再如,独立以后,非洲国家的后殖民地土地改革(尤其是坦桑尼亚的国有化改革),被认为是“非理性”“短见”的,破坏了粮食安全,因为这些土地改革主张“将土地的种族不平衡作为首要问题置于经济稳定之上”;抑或“白人私有土地经营方式优越于传统非洲人公社土地所有制,应该成为非洲主导方式”;或者“非洲小农户总是破坏土地的生态,而白人大农庄才是有效利用土地的最佳选择”“白人农场主的技术整体上远远超过非洲维生农业的农民,后者几乎无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等等。归根结底,很多主张源于白人相对于非洲人优越性的心理。这些土地改革贬低了非洲人世世代代积累的本土农业知识。可惜的是,这些深层观念因为欧洲人从历史上延续至今的强势而很难被“解魅”,很多非洲国家独立以后往往不由自主地采取更加倾向于白人大农庄的农业政策,商业、市场、银行信贷等都是向大农庄倾斜,而不是鼓励小农户和传统公社农业的生产方式。诸如安哥拉等国最终失败了的国有农场的实践,也多少受到这些流行观念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本来就处于劣势的非洲人小农户,独立以后一直在没有受到政府保护的环境中艰难成长,当然很难与白人农场主抗衡。有长期跟踪研究非洲农业的学者已经指出,历经殖民统治和独立以后的各种危机时期,非洲传统的小农户农业生产方式才是真正养活非洲大多数民众的根本。
是大农庄主模式好还是小农户模式好?关于非洲农业发展模式的争论,显然不仅是有关效率的问题,背后还涉及土地所有权斗争,即谁有权获得更多的土地生产资料从而扩大生产的权力斗争。在白人占有好地、大面积土地的国家,土地所有权仍是长时间困扰这些国家的主要难题。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在非洲其他国家激起了很大反响。南非、纳米比亚甚至肯尼亚等国纷纷出现了仿照津巴布韦激进土改做法的声音,而且每次经济不景气都会激发新一轮民族主义式的“非洲人要求土地权利”运动。虽然基本上都是主张不强行没收白人土地一派的政治家占上风,因为强行没收白人土地将加剧非洲的不稳定,并且强行驱逐经验丰富的农场主(他们有时雇佣多达200名工人)、把上千英亩的土地交给不熟悉大规模耕种的非洲人也是不切实际的(如津巴布韦土著人商业农场主联盟组织者诺夸姆齐·莫约就说,如果不投资并对非洲农民进行技术培训,重新分配土地很可能会导致农业生产的失败),但是不管大农场主模式还是小农户模式更加有效的争论从来就没停止过。
确实,有效使用土地是发展经济、解决以土地问题形式表现出来的种族问题的关键因素。非洲国家如果想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来创造财富,必须为非洲人的子女提供教育,使之适应工业化和技术发展,并实行某种有效使用土地的政策和解放市场的措施,以真正扩大非洲的经济基础,从而真正解决土地方面的种族问题。然而现实情况是,独立以来,非洲人精英阶层虽然逐渐掌握了更多的土地,但公社土地不允许买卖的习惯法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加之这些非洲人农场通常远离交通主干线,一般只能供应本地市场,而且以劳动密集型的方式为主;相比之下,白人农场主占据好地,而且距离交通枢纽很近;同时,非洲国家为了鼓励农业产品出口,基于粮食安全观而采取农业补贴等措施,实际上这些都客观上更能够惠及有实力的白人农场主,而非洲小农户反而更加没有竞争力。
有意思的是,随着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农业活动的减少、生物能源投资兴趣的增加,非洲大陆因为大量尚未使用的可耕土地和具备成为世界粮食中心的潜能而再次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主权或者私募投资家。西方跨国公司不断强化全球产业链布局,加大对资源性、战略性农产品市场的掌控力。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四大粮商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贸易,自然不能遗漏非洲市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种植大量用于生物能源作物的巴西、韩国和中东的投资者在非洲购地和租地数量较多。最近几年,非洲迅速成为全球农业投资热点。这些投资者都相信,只要扩大耕地面积,或者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非洲不仅可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甚至可以成为人类的粮仓。据不完全统计,许多外国机构已取得或者正在与非洲政府商谈的土地面积达5000万公顷,是英国国土面积的两倍以上,多数以长期租赁或购买的方式取得。
一时间,关于哪种方式能够更好地释放非洲大陆的农业发展潜力又一次成为热门话题:西欧、美国等传统农业出口国坚持大规模商业农业的模式,要求机械化和普遍使用化肥亦即推广所谓奥巴马模式;与此同时,另一派则主要来自非洲各国本土的力量,坚持认为应该投资小农户,因为他们的模式是更加尊重环境,以满足家庭粮食需要为出发点的生产模式。这一派还将大规模工业化农业视作小农户以及他们所依赖的土地和水源的威胁。汤普森教授在其为本书撰写的《农业发展与国际政策:非洲的21世纪替代方案》一文中指出,今天非洲农业发展的国际合作已成为国际公共政策问题,需要被广泛讨论,因为事关整个人类的未来。
按照达成共识的标准,2公顷以下土地的小农户(拥有2~4公顷土地的农户被视为中等农户),数量上占非洲总农户的90%,生产了80%的粮食。未来农业必定决定性地影响这个大陆的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方向,而小农户模式作为非洲农业生产体制的支柱形态,必须得到足够的政策重视和支持,以便为非洲快速增长的城市化提供更充分、更高品质的农产品和食品,同时通过提升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的品质使其进入全球市场价值链、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提升非洲自身解决贫困化问题的能力。
当然,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机械化大农业正在积极推进对于非洲农业的投资趋势。虽然大公司模式有弊端,但大公司确实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它们往往从上游到下游在很多领域、很多国家建成了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条,既分散了投资者的风险,又能快速地产生吸引力,特别是对于缺少生产资料的非洲小农户往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它们通过合同确实发挥了带动小农户技术提升和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效果。如果要引导更多小农户商业化的倾斜政策,还需要在制定国际政策时邀请这些非洲的小农户加入并全面地参与讨论,承认他们为全球粮食生产和人们更好地获取营养做的贡献,甚至承认保护本土知识培育出的新品种对于更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贡献——显然,影响和转变认知需要很长的道路,并需要有足够的接地气的科学研究和政策公开讨论作为前提。
实际上,讨论大规模商业农场还是小农户的生产模式更优,并不切中问题的根本。非洲农业生产危机的根源主要来自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健全的农业生产体制、不恰当的农业政策以及欠缺执行能力。另外,当前随着孤立主义和民族经济保护主义在全球的回潮,关于非洲农业的讨论充斥了太多外来投资者“兼并土地”的话语,妨碍了非洲国家制定和实施适宜的农业政策、保护本国国民土地所有权和发展机会,并且妨碍了小农户模式和大商业农场模式互补性地为非洲国家农业发展做出贡献,既无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创造就业、减贫,也不能成为有利于促进非洲工业化到来的引擎。当然,殖民时代以前与土地的亲缘关系、沉重的被殖民的历史记忆以及独立以来扭曲的发展经历,都使得非洲人对于土地问题特别敏感,对外来公司的介入天然地怀有抵触和敌意。这也提醒未来或者当下已经在非洲从事农业国际合作的实践者们,必须特别注意土地的敏感性问题。
四 新兴市场国家对非洲农业的南南合作
出于争取非洲大量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支持、建设社会主义国际阵营的需求,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对非洲的农业合作。冷战结束后,中国对非洲的农业合作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199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确定了要进一步地扩大对外开放。在此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开始走向海外,如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简称中农垦)、中国水产(集团)总公司等大型企业也进入非洲进行投资。
近年,中国形成了初步的“农业走出去”“农业走进非洲”的政策支持体系(详细见本书刘海方和宛如合作的相关章节论述),农业贸易+援助+投资的南南合作形式日益形成,并且与巴西、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呈现出很多相似性。
虽然国际上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认为新一轮对非合作热潮体现的是大规模购买和租赁土地,是“圈地”,是新的“瓜分非洲”,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正是激化这一轮“新帝国主义争夺”的罪魁祸首,但是新兴经济体普遍因为政治上“不干涉内政”原则而获得了与非洲国家广泛的合作机会。与此同时,近年来,新兴市场发展的历史显示,成功使人民脱贫的国家都依靠了农业革命,对粮食的生产、仓储、加工、销售和使用进行了系统的改进。非洲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欧洲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贡献巨大,而且巴西、印度和中国等都是重要的成功案例,利用农业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非洲急需学习中国、巴西和印度是如何在农业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的,而且要学习它们如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实现大规模人口的减贫。
我们之前已经出版了与印度、南非等国学者共同在赞比亚调研农业合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因此印度的案例没有收入此书。根据印度学者的调研,印度在非洲的农业投资是与印度当前国计民生的发展休戚相关的,即每年占国家外汇使用第二主要板块的粮食和食用油。印度总理专门组建了农业生产工作组主管此事,鼓励印度公司在海外购买土地进行豆类和食用油作物的生产,要“在海外购买土地种植农作物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并且预计“在15~20年中每年至少生产200万吨豆类和500万吨食用油”。印度进出口银行为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银行、金融机构及区域金融机构提供优惠信贷的条件是用于国家发展项目——农业发展项目自然可以使印度海外投资者顺理成章地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赢得优惠信贷和项目合同。这就不难理解塔塔集团等大公司和其他中小公司都竞相涉足非洲商业农业领域,从香料、茶到农用化肥等化学品,范围极广。很多印度公司原来从事建筑行业,现在已经涉足大型商用农场,这些农场分布在埃瑟比娅、马达加斯加、刚果(布)、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
值得注意的是,能够让印度在过去十多年不断加强与非洲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是印度已成为一个“高效能、低成本的创新中心”,并且有应对气候变化、自然资源减少、耕地质量下降、粮食需求增加等挑战的国际经验(即作为南南合作中的“价值”不断在各种国际发展合作的交流平台上被广泛传播和宣讲)。为期三年的“印美非三方合作伙伴计划”项目就是一例,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粮食安全办公室在美国政府的全球饥饿和粮食安全倡议(Feed the Future)项目下启动了这一合作,预期将把印度的经过检验的创新成果用于解决目标国(利比里亚、马拉维和肯尼亚等国)的粮食安全、营养不良及贫困等问题。类似地,在传统援助国加拿大、德国、日本、荷兰等,类似印美非三方对非合作都在进行。
类似,2003年卢拉就任巴西总统后,南南合作就成为巴西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并被继任政府所继承。巴西的外交重心转向非洲大陆以来,双边贸易不断增长,促进各种社会和经济部门发展的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拓展,同时投资性质的商业模式也在不断拓展。巴西在非洲的发展合作在农业和卫生等领域投入明显。巴西合作署最大的项目“热带草原计划”(20年里预算达到5亿美元)与“棉花四国”合作项目(Cotton-4 program,具体指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吸引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前者以提高受援国种子培育能力为目标,后者则宣称以提升这四个以棉花行业为经济命脉的国家的生产力、基因多样性和棉花行业质量为目标。像印度一样,巴西的对非农业合作经验明显更具有国际化的特点,有很多与日本的三方合作项目,不但利用了作为受援者接受日本的技术援助的经验,同时结合日本经验再创造出对非合作的方式;同时,巴西与联合国系统的各部门也相应设计了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巴西经验的合作项目。
与此同时,因为大量推进巴西自身从非洲市场获取生物能源方面的投资,巴西的对非农业合作饱受批判,被讥讽为“人没有吃饱之前先去‘喂养’汽车”;与此同时,“热带草原计划”虽然在莫桑比克大草原复制了巴西农业发展的经验,但是大豆和玉米的大规模产业化生产,也被认为导致了当地环境恶化和传统村落的消亡。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巴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和私人公司一起,通过巴西与非洲国家达成政府协议的方式促成了这些合作,服务于巴西自己的“乙醇外交”而饱受质疑,批判的声音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巴西国内的公民社会。这迫使巴西不得不重新调整与非洲国家的农业合作方式。
从本书收录的三篇有关巴西对非农业合作的文章中,读者还可以了解到巴西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马拉维进行农业合作的不同情况,三个截然不同的案例显示出非洲国家自己的自主能力、对于援助的认知和整个发展战略都大大影响了南南合作的效果。几位巴西学者认为,巴西专业人士应该增加对于非洲不同国情的认知和提高相应的行动能力,相信它们适用于同样是南方国家的中国,这些经验也正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值得参考的经验。
五 中国对非农业合作的新型实践及前景展望
非洲的经济增长曾经长期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推动,其直接结果是去工业化,同时“资源诅咒”风险、长期贸易环境恶化、“荷兰病”、国内上下游产业间联系不密切等问题恶性循环。今天的非洲国家已经形成一个深刻的共识: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是非洲摆脱贫困和饥荒的唯一可持续之路,其意义远超越减贫和粮食安全。为了当代,也为了后代,非洲需要设计一以贯之的、战略转型政策,改变世界的认知并确保非洲价值链与世界价值链紧密联系。总之,非洲国家对于农业的认知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因为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已不再将农业仅仅理解为农民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真正有利于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的活动。根据非盟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探索,前文提到的综合治理的发展战略还赋予农业更多的意义:农业既是创造就业、提高生活水平从而帮助人们自己解决贫困问题的产业,也是非洲避免陷入老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的最有可能的重点产业。考虑到联合国2030年议程不仅是向发展中国家也是向发达国家提出的新发展议程,今天讨论非洲的农业发展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就格外具有意义。
中国的对非农业合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完全不求经济回报的单纯援助开始,经历了援建很多大农场的时代,目前已经转向援助、贸易和对外投资并举的阶段。实践不可谓不丰富,教训也不可谓不多。当前中国对非洲的农业合作不像印度那种明确的与本国粮食和食用油安全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没有从非洲拿回一粒粮食”,但是也不能孤立地在农业领域里面决策——除了塑造国际形象的考虑以外,从实际效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农业合作也同样应该具有足够的外交关系和公共政策的视角,并充分考虑到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
目前,中非农业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来自认知层面,因此已经有的成功案例还有待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并作为正面案例广泛传播;课题组在这个研究撰写过程中,尽量完整地收集了中非农业领域的合作实践情况,从援助、商品贸易等各方面分析实施特点和目前的局限,选择的国别案例的考虑是:赞比亚是中国最早进行农业投资的非洲国家,津巴布韦是中国投资比较多且农业合作对于双边关系比较重要的国家,安哥拉是资金技术和当地人脉关系等资源都非常雄厚的大型国有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典型案例,而肯尼亚是分析民营企业怎样快速选取优势发展方向占领高端发展空间的案例。坦桑尼亚的剑麻农场打破常规,邀请了多年奋斗在一线的国有农场企业家结合自己的经营经验走进非洲并逐渐立足乃至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坦桑尼亚的剑麻农场的案例讲述了机遇与挑战,读来非常生动。这几个案例的国别情况和对华关系与目标都非常不同,希望这一组案例呈现的丰富性、差异性能够给下一步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足够的经验和知识,也希望为政策决策和实践者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总体而言,对于非洲农业问题,中国政府还必须有作为大国“增加援助但是不能止于援助”的认识。援助目标定位一方面要向非洲人提供尽可能多的知识技术和发展经验,另一方面要扶持和激发中国企业获得在非洲经营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经验,从而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即给当地人带来工作机会的、自主独立的国际化企业。因此,充分调动企业(既包括大的,更应该扶持中小规模的)的能动性,参与新时期的农业合作非常重要。三种合作形式应该有下一盘棋的整体观,要向达到“援助以促进贸易和促进投资”的方向努力。长远来讲,中国对非洲农业领域的介入,还应该有一些更具创新性的介入领域和介入方式,即从双边的角度应该多考虑与非洲本土已经开展的项目和实践的融合;同时从国际经济体系角度多开展一些南南合作层面的新项目和实践,以使中非农业合作的意义更为深远。
对于中国自身而言,讨论中非农业合作,显然既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实现“十三五规划”中更好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目标,对于促进非洲发展的意义更为深远。中国的农村正在经历第三次土地改革,只有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集约化经营有序推进,政府、资本、农民才能实现共赢。如果说有哪些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贡献于非洲当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意义深远的农业转型、发挥支持长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政府、资本和个体之间的协调和互动也许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条——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既需要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更需要“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必须起到主导、引导作用,做好规划,提供服务,在资本和民众利益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中国不但自身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时候需求非洲承接产能,也需要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与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分享,这本身也是中国稳固自身发展的根基。通过与国际发展伙伴的合作,印度和巴西都有了符号性的“价值”可以分享给广大发展中世界,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刘海方,北京大学非洲史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工作,作为访问学者在荷兰海牙社会学研究院、南非中国研究中心、加拿大卡尔顿大学非洲研究院工作。社会职务为: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南非杂志《非洲东亚事务》学术委员、泛非学术团体“非洲的亚洲研究学会”指导委员等。长期从事非洲和中非关系研究,已经发表了大量相关中英文双语学术作品。
宛如,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分行法律合规部。
刘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助理。
柯文卿(Kristian Secher),北京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硕士生,就学期间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助理。曾经在丹麦的学术期刊《自然》和《北欧自然》任责任编辑,现在为丹麦政府工作。
"非洲农业的最新发展与内生动力
农业在非洲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卡洛斯·洛佩斯 著 刘均 译】/3
农业发展与国际政策:非洲的21世纪替代方案【卡罗·B.汤普森 著 王筱稚 译】/19
非洲的城市农业:错过的发展机会?【戴安娜·李-史密斯 著 杨逸凡 译】/30
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增产与减贫【珍妮特·曼珍格瓦博士 著 沈晓雷 译】/41
解析赞比亚农业发展框架及其对小农户的影响【西蒙·恩戈纳 著 李家福 译】/56
新兴市场国家对非洲农业的南南合作
兄弟齐心?巴西在非洲的贸易、投资与合作【保罗·德·伦齐奥
朱理克·塞弗特 乔凡纳·佐科·戈麦斯 曼纳拉·阿辛卡奥 著 贾丁 译】/73
巴西在安哥拉卫生与农业领域里的南南合作【约翰·莫拉·丰塞卡
乔凡纳·佐科·戈麦斯 保罗·埃斯特维斯 著 贾丁 邹雨君 译】/85
国内体制和南南利益:巴西与马拉维和莫桑比克农村发展合作的成果
【卡罗莱娜·米朗斯·德·卡斯特罗 著 贾丁 译】/100
非洲崛起叙事与农业发展:深化中非关系
【萨义德·阿德朱莫比 盖迪翁G.加拉塔 著 聂晓 译】/117
中国对非洲农业合作的新型实践
从援助到开发:中非农业合作的支持体系研究【刘海方 宛 如 著】/141
安哥拉的农业发展和中国的角色【周瑾艳 著】/158
中国在赞比亚的农业投资情况及建议【宛 如 著】/172
津巴布韦农业国际合作与中资企业的粮食作物种植【沈晓雷 著】/185
中国与肯尼亚农业合作现状和除虫菊投资案例启示【胡姣汪 段 泳 著】/200
中国农业“走进非洲”的机遇与挑战
——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视角【刘 均 管善远 汪路生著】/212
Recent Development of African Agriculture & Its Endogenous Dynamic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African Alternativ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rol B.Thompson】/231
Urban Agriculture in Africa:A Missed Opportunity?【Diana Lee-Smith】/245
Zimbabwe's Land Reform: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Reducing Poverty
【Jeanette Manjengwa】/257
An Investigation into Zambia's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Framework and Its Impact
on Smallholder Farmers【Simon Ng'ona】/274
New Emerging Powers in African Agriculture
Solidarity Among Brothers?Brazil in Africa:Trade,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Paolo de Renzio,Jurek Seifert,Geovana Zoccal Gomes and Manaíra Assun??o】/295
Brazilian Health and Agricultural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Angola
【Jo?o Moura Fonseca,Geovana Zoccal Gomes and Paulo Esteves】/308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outh-South Interests:A Comparison of Brazil's Relations with Malawi
and Mozambique【Carolina Milhorance de Castro】/329
The Africa Rising Narrative 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Africa:Deepening China-Africa
Relations【Said Adejumobi Gedion G.Jalata】/352
China's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Countries
Angol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hina's Role【Zhou Jinyan】/377
Agricultur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Zimbabwe and Food Crops Cultivation of Chinese
Agribusinesses【Shen Xiaolei】/397
China's Agriculture Investments in Zambia and Suggestion【Wan Ru】/416
The Status Quo of China-Keny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Pyrethrum
Project【Hu(Annie)Jiao Dr.Wang Duanyong】/430
致谢/445"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
|